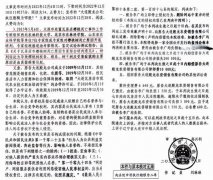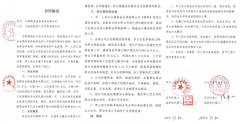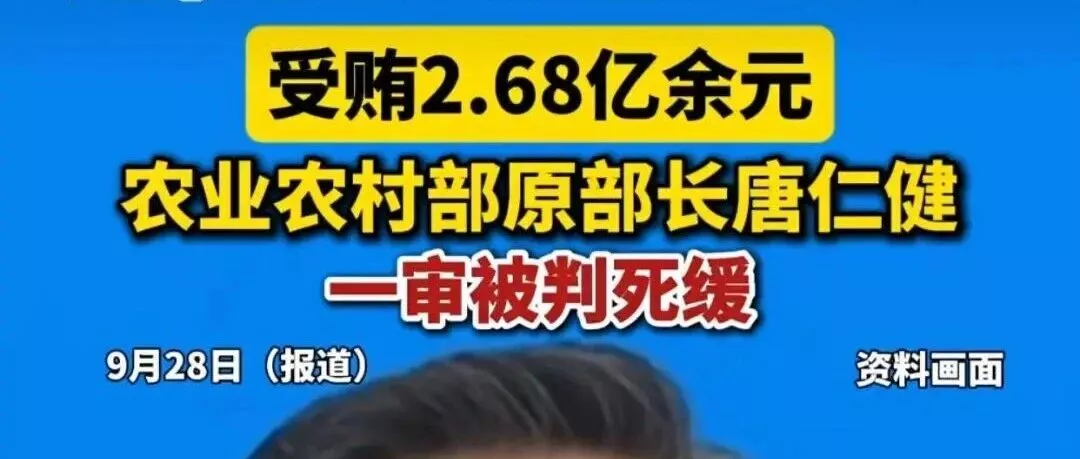
【题记】
有网友“投诉”成瘾。我写这个话题,前面已经3次“经用户投诉”而“暂时不可查看”。当然,用户一投诉一个准,这也是一桩奇事。但既然人家都投诉了,积极性必须支持。这是我对投诉界“行情”的理解。
我写了什么呢?我只是重复证明,农民可以“实质地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而不只是向村集体“承包”),我认为,如果能这样,则农民会更好,农业会更 好,农村会更好,国家会更好。
文后留言我全部放出来,可是,你不留言,你没有讨论问题的兴趣,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你就投诉。你相不相信,道理是讲明白的,不是投诉明白的。
我第3次修改以后,昨天晚上贴出来,今天上午十点,就被投诉准了,才一千个点击。其实我写得很用心的,辛辛苦苦写了三千字,才一千名朋友看到,难免感到失落。所以,我准备修改后贴第四次。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文章在公号上发得出来,就证明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是禁忌的话题,同时,也说明我用词是审慎的,没有触发敏感词。
我感觉到,有的朋友,一听说农民可以实质地拥有农村土地产权,就感到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尤其是一位名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网友,上来更不打话,只掷我三个字:“已投诉”,我跟他沟通,他也不理睬我,仿佛他的使命就是投诉。
下面是被投诉删除的文章大略——
让农民拥有“农田所有权”会不吉利?
1
我知道,城市土地所有权是“不可以讨论”的,它属于“全民”,是“路线问题”;而农村土地,包括农民的屋基地,属于“集体”——最基层的农业生产组织(只是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生产队,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事实也是这样。上个月,笔者两次发帖“议论农村土地政策”,文章能够发出来,就证明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虽然后来这两篇文章都“暂时不可查看”——系统是这样通知的,我也觉得“暂时”一词用得恰如其分,我也相信这是暂时的。
但事先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篇文章,得罪的都是网友。10月4日第一次贴出来,有网友在文后争论,观点对立,其中一位不讲武行德,上来就赠我三个字:“已投诉”。当然,应该还有“投诉”了没有向我报告的。总之,两个小时后文章就“暂时不可查看”了。
“此内容暂时不可查看”是比较轻微的处罚,可以修改后重发。我就不嫌麻烦,耐心修改,然后重发,这是10月17日了,这一次停留得久一些,也没有超过半天。
现在,我又修改了,准备重发。为什么我的脸皮这么厚,一而再地非要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显而易见被颠倒的问题,需要颠倒过来。
2
直接引起我的纠结的,是2025年9月16日网络消息,农业农村部长韩俊“重申”:“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严禁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报道还有一句——“韩俊部长特别强调,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和财产权益”
我觉得韩部长是一位内心柔软的人,他知道强调一下“初衷”就够了,至于结果如何,部长心知肚明,他知道公众也知道,不用再说,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
倒是一些网友杠上了。他们对农民可以拥有实质的土地产权“感到恐惧”,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怒不可遏。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让农民实际拥有土地权,如果让土地成为农民可以处置的资产,就会发生土地买卖,就会有农民“失去土地”,就会发生“赤贫”,就会回到旧社会,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因为这是教科书级的谎言。几十年前的教科书就是这么编的。直到现在,从贩夫走卒(农民工——破产农民,及其子弟),到大学教授,都会不过脑子,仅动腮帮子,背诵这一套。他们做出一副不接受反驳的样子,理直气壮,仿佛在守护弱者的命根子。其状令人惊愕。
3
事实上,农村土地所属,不是国家性质的关键。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带头大哥,十月革命后,在农村土地政策上也是有过争议的,并不是直接没收富家的土地充公。
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农村土地政策一直在变化。从“分田分地”,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人公社(初级社高级社),还有文革前,有过短暂的“包产到户”,后来作为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紧急刹车,强令禁止,然后到了改开年代,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土地政策都不一样,但都是社会主义。
可以说,到今天,农村土地政策还在“摇摆”,不然,某些“政策”也就用不着一再“重申”,而且在实践中,全国各地有自己的人创举(正如当年的小冈村)。
这都是农村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回想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或“默许”下,四川广汉悄然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标志着历史性的消灭了“人民公社”。而这样“重要”的消息,当时的报纸竟然不着一字。这无非是担心某些人转不过来弯——以为伤到了农村社会主义路线的根基。
接着“下放土地”(也叫“包干到户”,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原来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全部“租”给农民。由于这一政策的转变,立即使七亿农民摆脱了饥饿,城镇集贸市场农副产品不再紧缺,“凭票供应”迅速成为历史。
由于取得了这样的“伟大成果”,后来的报纸倒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本来“撤销人民公社”和“土地承包制”是两个连贯动作,前者因其“敏感性”避开了宣传。
农民“向公社租用土地”的期限,说是三十年,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是无限期。既然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公社土地,本身就说明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
而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又不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的直接后果,就是束缚了土地的潜力,让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有长治久安的的建设和投入,非当地户籍的人想冒险去农村修房造屋,也被锁死。
4
按现在的有限使用权,土地有时候不是农民的资产,甚至是负资产。例如,当农民由于衰老和疾病等原因而失去耕种能力的时候,无人接手,不能变现,不能抵医药费和护理费,但理论上还对土地负有“责任”——家庭责任承包制嘛。
最后,农村土地终究如魔术师手上的飞刀,当一代农民逝去,再回到“集体”,回到不叫人民公社的“公社”。这将是土改之后,农村土地的第二次“回归集体”这位虚拟的主人。
为了让农民“不失去土地”,就让农民“不拥有土地”,这套逻辑强大得令人无法反驳。
其实,于理于法,“有限产权”也应该可以“有限变现”,使它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尤其是“五保户”的“医保”。例如,农民“五保户”去世前将土地“交还集体”时,获得一定“补偿”。
今天触动我再次修订这篇稿子,企图再发一次的原因,是看到网上流传一个据说是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政府给城镇老人每月几千块钱,老人去世后,他们的房子归政府。也就是说,黄奇帆建议,政府帮助城镇老人用房产养老。
如果这一政策可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民用“责任地”养老?以体现农民在责任地上,除了责任,还有一定的权利?
5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开始,“集体土地”不是作为一种财产,而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身份标签,被按在农民头上的。
只有按这种逻辑,才能解释农民身份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或者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取消原身份所属的土地。否则,假使土地真正是农民的财产,难道考上大学或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接受一次财产剥夺的惩罚?
这便是农村土地的实质。
也就是说,当青年农民“及第”后便“失地”“失籍”,从此注定只能在房价高昂的城市老死,设若中年“去职”,或老来“思归”,均无再回到故乡居住的可能。陶渊明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归去来辞》只能是一篇痴心妄想。
在“离开故土便回不去”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有相反的政治传统。前清虽然跟今天一样,也是实行了官员回避制,县以上的官员都“外派”,但还有一个规矩是,官员告老都回原籍,不得在做官的地方置办房产。
今天就反过来了,不得在原籍买房盖房,你可以在任何城市置地买房,买多少房都可以国家正在鼓励,只要不在老家农村买就行。
在农村,花二十万可以盖一套宜居的独栋民居,而省城得花二百万,现在掉价了,也得一百万。所以,你想把城里的房屋卖了回老家住,省一大半的钱出来养老?不行。
6
说到底,“土地买卖”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买卖是纯商业行为,不涉及国家主权,不考虑购买者的国籍。
这里有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大约三个月前,媒体报道美国农业部“禁止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农田”。这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人不仅可以购买购买美国的房地产,还可以购买美国的农田。
这至少告诉我们,土地买卖并非不可想像。“退休干部”回村买地盖房并非大逆不道。这只是治理模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取决于观念,而跟国家主权无关(否则,把土地卖给外国人岂不等于卖国)。
2025年7月9日,外交部严正地谴责了美方,称那是“典型的歧视性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
而中国的农田呢,岂非歧视本村以外的所有人,包括从本村考学离开的前村民?
2025年10月3日草稿,15日重修,17日再修,11月9日再再修,11月11日再再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