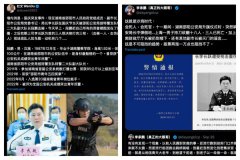目前,AI的浪潮正以几何级速度推进,甚至“996”的工作状态已经不再足够,“002”成了硅谷新常态。
当技术迭代从“按月”变为“按周”,传统的工作节奏已被彻底抛在身后。如今,硅谷的顶尖研究员与高管们普遍以每周80至100小时的高强度投入,奔赴这场前所未有的技术竞赛。市场竞争与AI技术的爆发式迭代,正在不断压缩研发周期,也让整个行业被迫在极限状态中疾驰前进。
硅谷100小时工作制真相:用命换AI进度条
在Anthropic担任研究科学家的乔什·巴特森表示,在生活和工作中,唯一能让他感到的兴奋的地方,就是Anthropic的内部通信平台Slack。在那里,他沉浸于同事们关于大语言模型与架构的讨论,不断探索新的理论与实验方向。
巴特森正是这群核心AI研究员与高管的典型代表。他们面临着无休止的工作,为了开发具备超人类智能的系统,不得不与看似永无止境的技术挑战赛跑。在硅谷各大AI实验室内部,顶尖研究人员与高管们普遍维持着每周80至100小时的工作强度。多位顶级研究员甚至将当前处境比作“战争状态”。
“我们基本上是要在两年内快速完成原本需要二十年的科学进步,”巴特森坦言。他观察到AI系统正在“每隔数月”就实现一次飞跃,“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入胜的科学课题”。

图:Anthropic研究科学家乔什·巴特森
来自微软、Anthropic、谷歌、Meta、苹果和OpenAI的高管与研究人员均表示,他们视自身工作为历史关键时刻的重要推动力。为此,他们既要与竞争对手周旋,又要寻找让AI普惠大众的新路径。
尽管其中不少人已积累巨额财富,但多位受访者表示根本无暇享受这些新获得的财富。在每周上百小时的工作制度下,谁还能找到挥霍金钱的空隙?
这场人才争夺战在马克·扎克伯格开始从竞争对手处挖角顶尖AI人才时就已升级,动辄数百万美元的薪酬方案彰显出这个相对小众的研究者群体已成为全球最珍贵的资源。如今,无论是公司还是员工本人,都希望每天压榨出尽可能多的价值。
谷歌DeepMind研究员马德哈维·塞瓦克近期坦言:“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工作,强度极高,而且似乎看不到终点。”

图:谷歌DeepMind研究员马德哈维·塞瓦克
据知情人士表示,某些初创公司已将“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明确写入劳动合同。但对多数企业而言,此举并无必要,顶尖AI人才自会被激烈竞争和对新模型可能性的好奇所驱动。
在Meta,新成立的TBD实验室成员被要求在公司门洛帕克总部扎克伯格办公桌附近集中办公。虽然全天候工作在硅谷历次创业潮中屡见不鲜,但世界级科技巨头出现如此极端工时确实罕见。
从“996”到“002”:AI竞赛走向“地狱模式”
在模型研发与产品攻坚的关键阶段,科技公司的工作强度往往突破常规。当业界熟知的“996”模式(早9点至晚9点、每周六天)已无法满足竞争需求,一种被称为“002”的极限工作制应运而生——从午夜至次日午夜全天候待命,周末仅有两小时休息之机。
这种高强度工作模式主要集中于各企业的核心团队。他们肩负着改进核心AI模型、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新产品的重任,常常在深夜继续攻坚,甚至在普通薪资同事早已下班后仍坚守岗位。
尽管多数人坦言这种工作节奏令人身心俱疲,严重影响了与家人朋友的相处时间,但他们同时强调这是“自主选择”。正如谷歌研究员塞瓦克所言:“当灵感不断涌现,而你又深知这是在和时间赛跑时,自然不愿放过任何创新可能。”
为适应这种近乎全天候的工作状态,硅谷企业纷纷推出配套措施:周末提供餐饮服务,确保关键岗位始终有人值守,设立短期轮值的“值班主管”监督模型产出,或安排长达数周的产品开发督导期。
费用管理初创企业Ramp的信用卡交易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旧金山地区餐厅在周六中午至午夜的外卖订单量显著增长,其增幅远超该地区往年水平及其他美国城市。这组数据背后,正是无数科技工作者在周末依然奋战的身影。
技术转化周期从“数年”压缩至“朝夕”
微软AI体验首席产品官阿帕尔纳·琴纳普拉加达指出,虽然她亲历过科技行业多次重大转型,但本轮AI浪潮的紧迫性截然不同。

图:微软AI体验首席产品官阿帕尔纳·琴纳普拉加达
她对比历史经验表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还是iPhone引发的移动互联网变革,技术普及周期往往长达十年以上。然而,在AI领域,仅仅几年时间,财富500强企业中就有90%已经在采用AI产品。”
更关键的是技术转化周期的急剧压缩。在AI时代,从研究突破到产品发布之间的时间,已从过去的几年,压缩到了“周四和周五之间的那段空隙”。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出巨大市场需求,迫使所有企业全力冲刺。
面对超负荷工作压力,琴纳普拉加达将管理者承担的额外职责称为“第二班岗”。为提升效率,她为自己开发了AI工具集,其中包含能实时优化工作流程的浏览器插件。每次新建标签页时,系统都会智能提示如何利用AI改进当前操作。
“业界热议的24/7工作制存在本质误区,”琴纳普拉加达强调,“持续运转的不该是员工本人,而应该是他们驾驭的AI系统。”
在Anthropic,巴特森揭示了AI研发的特殊性:由于模型进化轨迹难以预测,传统工作计划常常失效。这更接近自然进化过程,而非按图施工的工程项目。这就像直到训练完成前,你无法预知结果,测试前不了解具体表现,甚至部署后仍存在未知变量。
巴特森将当前工作强度与疫情期间参与病毒检测实验室的经历相提并论。与当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使命感相似,他对开发符合伦理、与人类价值观一致的AI充满热情。他们正在证明,人类理解能力的提升速度可以超越模型迭代速度。
谷歌研究员塞瓦克坦言,看到顶尖AI研究者凭借智慧与付出获得应有回报令她倍感欣慰。“我们这些‘技术宅’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她说。
然而在这片繁荣景象之下,塞瓦克敏锐地察觉到某种失衡。她发现尽管行业蓬勃发展,大多数同行却未能建立起健康的生活节奏。“至今没有人真正安排休假,”她称,“大家依然挤不出时间陪伴至亲好友,无暇发展个人爱好,工作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
“996文化”在硅谷卷土重来 硅谷现新型“包身工”
随着AI领域的竞争持续升温,硅谷多家初创企业公开推崇以“996”为代表的硬核工作制,甚至将其塑造为一种团队美德,更有投资机构开始建立评估企业工作强度的“奋斗指数”体系。
初创公司Browser
Use的联合创始人马格努斯·穆勒选择与团队成员共同入住旧金山高档社区的“黑客之家”。这种聚居模式让他们即便在凌晨一点也能围绕白板展开头脑风暴,随时捕捉关于AI智能体的新灵感。穆勒直言,他期待招募的是对工作“上瘾”的人才,并将这种状态比作“终日沉迷电子游戏般的投入”。
为最大限度凝聚团队专注力,旧金山AI初创公司Sonatic为首批员工提供包括免费住宿、送餐津贴乃至约会平台会员在内的全套福利,但对应的是要求员工每周七天到岗。
更为直白的是AI公司Cognition,他们在招聘过程中就明确告知求职者需要适应长期加班的文化。公司CEO斯科特·吴在社交媒体上坦言:“我们拥有极端的绩效文化,招聘时开诚布公是为避免日后产生误解。”
这种趋势已蔓延至招聘文案的每个细节。人才匹配平台Mercor在招聘启事中,明确要求应聘者必须接受每周六天工作制,并标注“此要求不容协商”。纽约AI企业Rilla则在岗位描述中同样直言不讳:无法承受每周70小时工作强度者请勿投递简历。
部分创业者对“996”工作制持更审慎的态度。旧金山AI企业Optimal联合创始人兼CEO伊巴·马苏德作为连续创业者,提出了差异化见解。她指出,在竞争激烈的AI领域,创始人团队确需保持高强度工作节奏,但这一标准不应简单套用于全体员工。

图:Optimal联合创始人兼CEO伊巴·马苏德
“面对行业发展的迅猛势头,时间投入是不可避免的,”马苏德坦言。但她同时强调,团队管理应当保持灵活性,“我们更看重成员的自发投入,这种内在驱动力产生的效能远胜于强制性的工时要求。”
在产品攻坚的关键时期,团队会自然进入集中工作状态。马苏德区分了两种工作模式:“临时性的全员冲刺与制度化的996存在本质区别。我们追求的是在保持团队持久创造力前提下的弹性协作,而非单纯的工作时长堆砌。”
当AI永不眠时,人类需要学会关机
当硅谷沉浸在高强度工作的狂热中,一种冷静的反思声正从经验丰富的创业者群体中传出。当整个硅谷都在高呼“燃烧自我”时,这些见证过多个行业周期的资深人士泼下了一盆冷水。
资深创始人们指出
,过度美化“996”文化最终将导致工作倦怠,并严重限制企业的人才储备,因为经验更丰富的员工可能不太愿意无休止地工作。
风险投资公司Menlo
Ventures合伙人迪迪·达斯直指问题核心:“超长时间工作往往滋生更多延误,而非提升效率。”他观察到,推崇这种工作模式的多为年轻创始人,“他们尚未领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每周工作40-50小时的产出,往往远超那些工作80小时的人。”
这种反思在具体案例中得到了印证。当Browser
Use的联合创始人穆勒在社交媒体发布包含“996”条件的招聘帖后,尽管获得5.3万次浏览,却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无异于“没有生活的奴隶”。
曾成功创立Wrike并以22.5亿美元将其出售的安德鲁·菲列夫,用亲身经历佐证了这一观点。他直言,硅谷对“每周100小时工作制”的迷恋实为“自我毁灭”。“创业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他强调,“长期维持这种工作强度根本不可持续。”
尽管AI代表着重大技术变革,紧迫感确实存在,但菲列夫提醒道:“人类生理与心理的客观规律从未改变。可持续的成功,依然建立在强大团队、优质决策和足够持久的坚持之上,唯有时间才能让优势真正显现其复合效应。”